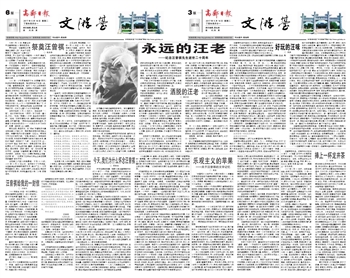我观瞻过多帧汪曾祺老的照片。有扎着围裙下厨的,有伏案作画写字的,有与友人交谈的,还有那张为无数人点赞的“一对老鸳鸯”(与其夫人泛舟高邮湖)的照片,但一直存活在我脑海里的还是那帧身体微倚、指夹烟卷、手托额头的照片。
不知道是哪位大师拍摄的,也不知道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抓拍的,拍得太生动传神了。照片上的汪老,神清气爽,淡定自若,指间袅袅升腾的烟雾,顶上稀疏银白的头发,额上数道深深的皱纹,透出十足的洒脱不拘与自足祥和。
1981年,我在高邮师范读书的时候,曾聆听汪老的讲座,那该是老人阔别家乡数十年后的第一次回乡。那时我们对作家对文学全无概念,更不知道台上的老人就是京剧《沙家浜》的创作者之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上的文娱宣传队上演过《沙家浜》选场,村里有一点文化的年轻妇女大都能哼上“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其小众的文化表达,达到了大众的普及效果。我最早拜读的汪老作品是《受戒》和《大淖记事》,感觉与自己在中学读过的文章不同,何以不同,不知所以。
此后一直在乡下的中学教书,很少获得汪老的消息,更没有机会与汪老有过哪怕一分钟的零距离接触。2013年,因工作需要,到河北考察鸡鸣山驿建设。组织者行前说,此番还将到汪老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看看,我很高兴。后未果,有点失望。
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汪老的认识了解。我通过拜读汪老的作品,走进汪老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别人的文章和讲述,了解汪老的别样人生。
我心目中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普通人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作家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名人的汪老同样是洒脱的。
汪老的为人是洒脱的。正因为他的洒脱,在家里“没大没小”“多年父子成弟兄”,营造了亲情浓浓的家庭环境,甚至在他露出得意的“尾巴”时,小辈们会浇上一盆冷水。正因为他的洒脱,在下放到河北农科所劳动后,苦中作乐,边画马铃薯图谱边享受烤马铃薯的美食。能将苦难转化为快意人生者非洒脱不能为。正因为他的洒脱,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朋友。正因为他的洒脱,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激起更深的尊重。据说某一次回家乡,一家饭店请其题写店名,要求写“某某大饭店”,汪老略一思考,说:“你这家饭店哪能说是什么大饭店。”“大”字终没写上。此事是否属实,没有考证,但发生在汪老身上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他于人于事,自有认识,自有理解,不会囿于外界的长长短短。
汪老的为文是洒脱的。他从没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什么“主义”“流派”的标签,也不刻意模仿某一位某几位中外大作家的套路创作。他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但绝不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几不从事文学创作),他按照他认识的世界反映世界,他按照他理解的生活讲述生活,他按照他掌握的小说创作小说。诚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太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确实,汪老的小说少有激烈冲突的情节,像陈小手身后挨一枪的情节在汪老小说里是罕见的。有人据此遗憾地表示:汪先生的小说难以改编成电影电视。他以洒脱无拘的为文风格,耕耘出一片崭新的文学田地,给近乎窒息的文学空间吹进清新的空气,赢得众多读者的追拜,直到他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各种集子仍在不停地出版,这是许多现当代作家难以比肩的。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称汪老为“被遮蔽的大师”是恰如其分的。
名人汪老也是洒脱的。文革结束后不久,汪老即推出若干篇“小桥流水”般的小说,在文坛上形成了轰动效应,成为知名度极高的作家。但是汪老不摆谱、不矫情,一如常人生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他回家省亲,仍依旧礼给继母行跪拜之礼。老乡朋友上门,他依然扎起围裙下厨。即使是自家房产没有落实政策,他也没有端起名人架势与政府论理,仅仅写了封寓理于情的书信。有人为此愤愤不平,然而,汪老没有喜怒于声,平和如初,一如既往地推介高邮,提携后学。那首由汪老作词的《我的家乡在高邮》,一直在高邮大地传唱。
于一个人来说,洒脱是什么?汪老以他的为人为文告诉我们:洒脱是守得住、拿得起、放得下,不为艰难所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左右,活出自己的快乐,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
洒脱是一种风度,一种胸襟,是底气骨气,也不乏一点点傲气。
我从不奢望通过阅读汪老的作品而成为名人名作家,倒是想通过反复拜读其经典作品,获得一点洒脱的智慧,继续自己的五味人生,仅此一点就足够了。我知道:写作不是所有人的营生,更不是人生的全部,业余作者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