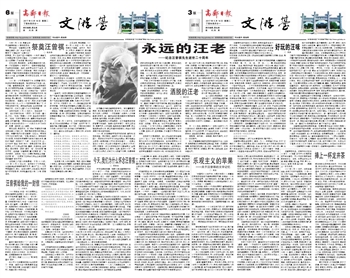今年5月16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忌日。
贾平凹称“汪曾祺应该是建庙立碑的人物”,先后为汪老题写了“文章圣手”“山高水长”的赞语。家乡汪迷乃至乡亲都有一个共识,高邮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也难出一个这样的文学大师。汪公让同辈人及后来者“高山仰止”。
初见汪老,是在南京。他是受高邮政府之邀,第一次返回阔别42年的家乡,在南京短暂逗留,然后乘客车回邮。当时,他的声名远不及后来,没有专车接送,没有专人安排食宿。其时,我被省文联借用,尽管没有接到县里关于接待的指示,我还是十分兴奋,主动揽事,缘于想见见汪老,并为其提供方便。
1981年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带着《雨花》杂志社开具的住宿证明,陪汪老去白下饭店入住。一了解,普通房间客满,每天10元以上的房间还有。我不假思索地问道:“这种房价好报销吗?”汪老望望我,没有开口。我又问:“这房住不住?”汪老只说一个字:“住。”待到汪老回乡见到同学刘子平,知道刘是我的老师,对我颇有微词:“你的学生怎么这样说话,愣头青似的。”刘老师悄悄告诉我:“待人接物还得学学。”县里无人授“权”,那时,我在宁驻勤费每天只有八毛,认为10元的房间是“高价”了,才引起汪老的不悦。得知后很后悔,给汪老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这成了心里久久化不开的疙瘩。
汪老于当年10月10日返乡。在他住的“一招”,他谈笑间对我说:“《雨花》发了你的一篇小说,不长。”我说:“原稿七八千字,登出来只有四千字。”他说:“伤筋动骨地大砍,编辑也可能有他的道理,你琢磨琢磨。”想到日后他给陆建华信中,对高邮文学创作的评价——“大体仍处于习作阶段”,可谓一语中的,让人信服。
再见汪老,是在扬州。我“领命”专程赴扬州请汪老作第二次回乡行,用的是政府刚买的绿色上海轿。身着米色风衣的汪曾祺一口应允:“哪有到了家门口不进家门的。”于是,乘车返乡。刚走到扬州大桥西,开车的朱师傅要为新车办相关手续,请我们“稍候”,可却成了“久候”。我忐忑不安,让一位大作家“枯坐”车中,咋办?倒是汪老不急,吞云吐雾中,谈及文游台的对联、匾额。我告诉他,主体楼上,西边是李一氓的“湖天一览”,东边拟用“嘉禾尽观”。他问道:“你看是用‘嘉’还是用‘稼’?”我没法肯定。汪老说:“无论从实景还是词性上来看,应该用‘稼’。”这便有了五年后文游台上由汪老题写的匾额“稼禾尽观”。
汪老第二次回乡时间最短,不足20小时。1986年10月28日上午,连续举办了文史讲座,与在邮演出的德德玛等艺术家、棉纺厂工人、文艺界同道联欢、倾谈。他目光炯然,谈吐自如,早已定格为历史的影像,深深地叠印在乡亲、“乡党”的脑海中。
三见汪老,是在高邮,1991年9月30日至10月7日,汪老第三次回邮,活动多、走访多、欢聚多,其情浓浓,其乐融融。全程除了亲戚相伴,皆由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朱延庆等人陪同。从缫丝厂汪老为文学新人发奖、签名、题词,到在市委党校举办文学讲座时,座无虚席,连80多岁的老夫妇都饶有兴趣地来聆听他谈语言问题;从市领导随汪老回家看望继母——任氏娘,当时继母已倚门而待,到老邻居唐四奶奶一句“你现在混得不错啊”,汪老说“托您老的福”;从克明带路去寻觅、观赏汪父的画,到汪老夫妇游湖,他自称“高邮湖上的一对老鸳鸯”,都成为众人皆知的佳话。
在汪老的住处,我受邮中一位老师之托,将他写的评价汪老的论文让汪老看。汪老带起老花镜认真地翻看了,然后说:“这位老师下了不少功夫,但是重复他人之言不行,要有自己的见解。”就在那天,他把几本外文版的己著赠送给文联,我郑重地接过来。
《鉴赏家》中卖水果的叶三原型陈富贵的儿子陈广元拿来几幅王陶民的画,让汪老鉴赏。汪老看了一番,当众评价王画的笔法、意象、风格,又听了陈广元讲王陶民的逸事、趣事,引得大家乐不可支。有一天下午,夕阳西下,我一个人陪他看正在修复的宋城墙,发现有些宋城墙砖上烧着工匠头的名字。汪老说:“这不是为了扬名,而是表明责任,这是一种担当。”接着,他诵起自己的诗作《宋城墙》:“留得宋城墙一段,教人想见旧高邮。”正是无数篇有关旧高邮的精品力作,为汪老奠定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97年5月16日下午,北京友谊医院的太平间,成了我与汪老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突然“走”了,面色灰暗,安静地躺着。本以为的一次拜访倏忽间成为永别,令我猝不及防,我只能以三叩首敬拜之。
如今,值纪念汪老仙逝20周年之际,试作祭文一篇附后:
汪公曾祺,星斗其文。爱国爱乡,赤子其人。
文学大家,学贯古今。才华盖世,四海清芬。
大师教诲,刻骨铭心。拜师从文,于师不逊。
佳作尚品,妙手绘春。《受戒》传播,天籁之声。
书画诗文,雕形铸魂。塑造形象,入木三分。
人性为本,真情传神。有益世道,一往情深。
教化人心,隽永天真。乐为人间,频送小温。
瞩望后生,辛勤耕耘。兀兀穷年,久久滋润。
曾祺辞世,佳话遗痕。祭奠汪公,泪不能禁。
魂萦梦绕,不忘汪恩。桑梓乡亲,永远前进。
“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是的,在我们高邮乡亲身上,都可能延续着秦、汪的基因,都可能连接着乡贤的文脉。这对历史文化名城发扬传统,继往开来,挹古扬今,努力奋进,是至关重要的,它应成为临政莅事者的头等大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