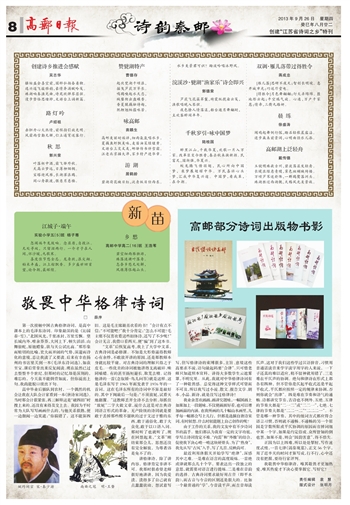第一次接触中国古典格律诗词,是高中课本上的毛泽东诗词。印象最深的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那形象而贴切的比喻,宏大而开阔的气势,深邃而诗化的意境,总让我读了又要读。后来有幸在扬州的书店里买到一本《毛泽东诗词选》,如获至宝,课后常拿出来反复阅读。现在虽然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但那时的记忆却是深刻的,难忘的,今天虽不能倒背如流,但你说出上句,我尚能脱口续出下句。
高中毕业后插队到农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大队会计家看到一本《唐诗宋词选》。当时那会计很紧张,再三解释这是“破四旧”时搜上来的,还没有来得及交上去。我因为平时常为大队写写画画什么的,与他关系很熟,便一边翻阅一边笑道:“你搞错了,这不能算四旧。这是毛主席最喜欢看的书!”会计有点不信:“不可能吧?”我十分肯定:“怎么不可能?毛主席不仅喜欢看这些旧体诗,还写了不少呢!”会计无言,我借口看两天,便“骗”到了这本书。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中文系,古典诗词是必修课。不知是大形势逼得教师心有余悸,不敢放开讲的原因,还是那教师本身就比较平庸,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只得之于皮毛。一些优美的诗词被他讲得支离破碎、味同嚼蜡。有的甚至扬短避长、取芜去精。记得他讲的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是这样。这是毛泽东写于1965年而发表于1976年的一首词,这在毛泽东所有的诗词中不算是最好的。其中下阕最后一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教师丢开全诗不去分析,却抓住“放屁”二字大做文章,说什么这是对古典诗词语言形式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诗词就是要敢于丢掉那些酸不溜秋的过于文过于雅的东西,敢于通俗化,敢于大众化,敢于以口语入词。那时听了也就听了,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刚结束那会儿,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为尊者讳是免不了的。
讲格律诗,除了讲内容,格律肯定非讲不可。我那时很希望老师很好地讲讲,因为我爱读,读得多了自己就有点蠢蠢欲动,想试着写写,但写格律诗的束缚很多,主旨、意境这些高要求不说,语句最起码要“合律”。只可惜老师只知道照本宣科,讲得大多数学生云遮雾罩,不明究里。从此,我就对中华格律诗词有了一种敬畏感。总觉得这种文学样式可望而不可及,所以我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小品、新诗,就是没写过格律诗!
我业余喜欢画画,画讲究题咏,一幅国画上如果加上一段题咏,不仅使画面好看,也可以增加画面的内涵。在我所画的几十幅山水画里,几乎每一幅都会写上几行,但都是选摘自唐诗宋词,有时候想,什么时候能题上自己创作的呢?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的文友中有不少诗词界的高手。他们都认为我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学写古诗词肯定不难。“内需”和“外推”的结合,促使我下决心啃一啃这块硬骨头。为了“热身”,我先从写“古风”入手,写了几首,反映尚可。
最近利用休假天开始学写“绝律”,深感其中之难。一是难在语言的高度凝炼。一首绝或律就那么几十个字,要表达出一段独立的意思,就需要对语言进行提炼。二是难在音韵的选择。古典诗词要求最好用古音(即平水韵),而古音与今音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一个最普通的“学”,今音读平声,而古音却读仄声,这对于我们这些学过汉语拚音,习惯用普通话读音来学字读字用字的人来说,一下子还真的难以适应,稍不留神就用错了。三是难在平仄声的协调。绝句和律诗在形式上都各有四种,但不管你是仄起平收式还是平起平收式,平仄都应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协调,否则你就会“出律”。四是难在节奏和语气的通畅。诗都讲究节奏,古诗也不例外。五绝、五律的节奏大都是“二一二”或“二二一”,七绝、七律的节奏大都是“二二一二”“二二二一”。不管是哪一种节奏,其中的组词方式都应符合语言习惯,否则就不通畅。不通畅的另一个原因是字数所限或平仄协调的原因而省掉词组中某一个字,如果是约定俗成、众所皆知的倒也罢,如果不是,则会“因韵害意”,得不偿失。
正因为以上四难,所以处处掣肘,写作速度忒慢,一首七律《谒秦观墓》,正文56个字,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才算写成,行不行,心中还没有把握,要待行家评判。
我敬畏中华格律诗,唯其敬畏才更加热爱,唯其热爱才下决心要掌握它、写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