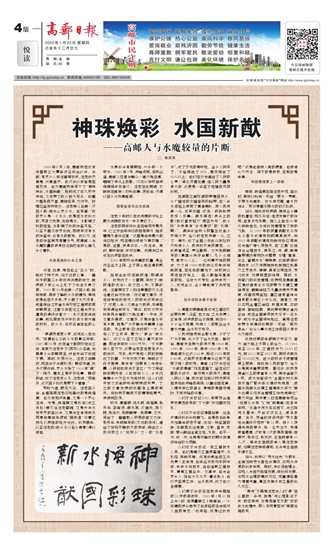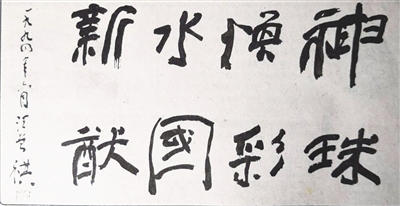1994年6月1日,高邮市在北京中国职工大厦举行经贸洽谈会。会前,有家乡人向汪曾祺求字,汪老欣然挥毫,兴趣盎然。此次会议宗旨是招商引资。他为高邮市委写下了“神珠焕彩,水国新猷”,既钩沉了悠久历史传说,又点赞了故乡巨大变化。此幅为整张四尺宣,横排竖写,为行书。按理应留存市委办。汪老早从他第一次回乡前,就关心家乡水。他写道:“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风格。”以至外国汉学家也说,即使写没有水的作品中,也有水的感觉。我以为,汪老的作品常荡漾着水气,那高邮人与水魔较量的浪涛已经拍打他的心扉几十个春秋。
水患是他的心头之患
纠结、忧患,早在他上“五小”时,就成了抹不去、绕不过的心痛。一篇关于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堤的作文,就表明少年心头上扎下了关注水患之根。1981年10月他第一次回乡前,就向亲戚、同学了解故乡水的情况,常说的是他在外多年,家乡闹了水灾没有,或者向任江苏省水利厅总工程师的同学韩同生(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与苏北灌溉总渠设计者之一)多次在京询问此事,或托同学刘子平找点水利方面的材料。故乡水,日夜流淌在他的心中。
“悬湖荡漾思乡梦,运河流入枕边书。”可谓他心系故乡水的真实写照。1981年10月,我在省文联民协驻会工作,有幸为汪老开了《雨花》介绍信,与高高个头的韩同生,送他去白下饭店下榻。其时,秋雨纷纷。汪老又问韩总,现在会不会闹秋汛?韩总笑道,我多次同你说,家乡水除了1954年“闹”了一阵外,基本上是平安无事。韩总的话,成了汪老定心丸,汪老说:“那就好,这次回乡我还是要下乡看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汪老回乡后,全程陪同汪老实地踏访的是肖维琪。他水利知识丰富,又是一个热心汪迷。于是,肖维琪又是找来《运工资料》等交给汪老翻阅,又是参与水利专家的座谈会,又是与王承炜或仇雨亭到高田车逻和“锅底洼”川青这两处代表性的地方采访。收获甚丰,以至汪老的《故乡水》《他乡寄意》得以问世。
水患似乎有周期性,六十年一个甲子。1991年7月,洪峰迭起,来势凶猛,高邮父母官与群众一道力挽狂澜,唱响了浪尖上的歌。终究以炸坝泄洪保堤保平安告终。汪老在此期间,不断向在邮亲人打听此事,获悉后,才得以回乡泛舟高邮湖。
固若金汤与众志成城
汪老少年时代在运河堤的子埝上踢水洗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汪老的同学许长生在电视专题片中、伫立于当年决口的挡军楼处,指点着堤外告诉记者:“这里是当年最大的决口地方,现在堤内被称为荷花塘。”是的,往昔,浪涛滚滚,一片汪洋。其时,荷叶田田,平安无事。运堤决口与运东内涝皆在此中。
1991年那场与洪魔的较量,是各行各业齐上阵、上下同心挽狂澜的凯歌。
当年主战场在新民滩(即湖滨乡)。我走访了一个星期,写成了《新民滩的沉浮》,此文已入书,不再叙说。汪曾祺笔下人物汪厚基的女儿汪洛看过后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好,好在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写到位了,还把人与人之间合力抗洪、夺得胜利写得恰到好处。”其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力挽狂澜》一书中,好文章多得很。文章好,不是作者水平有多高,而是广大干群与洪魔搏斗出来的。书上载有《欧洲时报》一文,乃华人丁立所写,题为《“粮仓”进水后》。该文介绍了三垛乡遭灾的惨重,即往年可收2400万斤,一下子跌到七百万斤,这要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创伤。对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成了救星。为发放救灾款,早就订了许多制度,其中有“如果有人中饱私囊,人民和政府决不答应!”为了保证新学期开学,从政府到个人,十天内筹集十六万五千元和材料,让人们在开学之初能够听到琅琅读书声。丁立的文章发表时还配有上课的照片。将我市干群抗灾的精神和勇气,传递到欧洲。
杨杰、葛国顺、姚永明、肖维琪、张月华、邵奇波、胡永其、佟道庆、陈冬梅、张廷豹、张振群等一批同事、文友,写出了一篇篇载入史册的佳文力作。张月华、朱明辉写的《不沉的绿洲》,道出了甘垛干群抗灾的艰辛,保证这个扬州市三个“无坝乡”之一的“水洼子”,成了不沉的荷叶地。全乡人民笑了。水稻保住了90%,棉花保住了80%以上。他们在文末道出了人民的心声:“造化尽管无情,但人民力量是伟大的,这便是一条坚不可摧的风雨长城。”
在湖西三面环湖的菱塘回族乡,乡广播站的女播音员杨晓琴,在一条水泥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游弋抗洪第一线,边写边播,还来一段快板表扬好人好事。胡永其在《浪尖上的歌》称这宣传船为“诺亚方舟”,称小杨“多像具有‘补天意识’的‘女娲’啊!”。湖滨派出所小民警王成舍小家保大家,始终钉在抗洪第一线,立了一等功,成了全国公安战线抢险救灾先进个人、抗洪救灾爱民模范。从此荣誉迭至、声名鹊起。文友张振群写的《清障分洪好后勤》,几个小细节,感动众人心。一位叫夏宏祥的同志,为了将1000米胶质线紧急送到新民滩,在无车的情况下,将胶质线绑在自行车上,一路小跑推车直奔目的地。经受大灾考验,全市未死一人,运河全线,各乡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治水功臣永载于史册
从建国初期高邮县运河工程总队主要负责人冯坚、杜文白、工务负责人王承炜、许洪武的治水保堤,到如今一个个治水英模、先进个人的敬业治水管水并重,治水功不可没。
从抗洪排涝到治服水患,少不了广大干群,也少不了治水功臣。解放后,高邮发生特大的洪灾是1954年、1991年、2003年,其中2003年7月,高邮湖水位达9.52米,超过1931年的9.46米,这超历史的最高水位标尺竖起了惊人的叹号。高邮人们不会忘记“水做的高邮”刻在屋檐下、留在记忆里的水印子。面对特大的洪灾,高邮人民以人墙、抛放巨石和以树木绑好挡浪迎战洪峰的奔袭,以重任担在肩、人堤共存亡的信念,奏响的是固守堤防、不可动摇的乐章。
人们不会忘记1951年荣获治淮劳动模范称号的“丁大锹”参加国庆观礼。
人们也不会忘记建国后第一任生产建设科科长郑鹏飞。他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犹如一块坚固的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文教、宣传、支前,带头献出全部土地、水利。他干一行,成一行,尤其是对解放初期水利建设作出较大贡献。
人们还不会忘记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高级工程师詹福宏、汤松熔、李新月等。还有我熟稔的工务负责人王承炜,他毕业于扬州平民中学,未学水利技术,但他谙熟工程技术,精通工程业务。文革中,他与全家十人(除他大女儿外)遭受批斗,他仍然坚持工作。治水抗洪,成了他终生课题。
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抗洪中牺牲的21岁的吴志平。1991年7月31日上午9时,在测量第三个断面后,一个无情的浪头卷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和对人世的爱恋。“我年轻,还是让我去吧!”这是他告别人间的遗言。他被追认为烈士。倒下的是标杆,竖起的是丰碑。
科技管理更上一层楼
早年,肖维琪在陪汪老参观、座谈时,常可以听到一句话:“要水一声喊,不要水关闸板。放水穿花鞋,看水打洋伞。”那只是管水用水的初级阶段。
如今,相关资料表明,早年各乡镇的机灌站(现水务站)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且有多元发展。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水利科技管理有了质的飞跃。从1991年的预置装配式系列化小型水式建筑物钢模具技术,到2011年装配式建筑物新材料应用研究与推广等七项技术,在“三高”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满足江、河、湖、库等重要堤防库坝防渗需要,处理“管涌、流土、窨潮渗水”等隐患,农田鼠洞成洞技术,以及深层搅拌机械相应机具及工艺技术,等等,具有实用性好、节约成本、效果明显的作用。同时,水利部门的科技管理,还表现在高邮灌区建成信息化系统的野外水情工情遥测站、闸群遥控及水量决策专家高度、远程视频监控、灌区信息查询与信息服务等五个子系统。简言之,可以实现全灌区遥控,数据共享、实时查询、智能控制。其成果或填补省内空白,或在全国单项技术处于一流水平,或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套用汪老称赞水利建设成果的一句话:“厥功伟矣!”也令从事水利工作的回乡游子大为惊讶。
科技成果的丰硕离不开实力、智力、能力和上下同心的给力。从1991年至2010年,工程投资为12.81亿元,而2011年至2017年,其投资飙升至20.89亿元。巨大的投资才使管理更上层楼。而科技人员的智力、给力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据统计,我市获得省以上的荣誉有20项,其中省部级5项。被水利部评为“全国农村水利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县”,被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评为“南水北调系统资金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最为突出,其中意义已在高邮电视台《壮丽七十年 飞“悦”新高邮》栏目中体现,“北澄子河水东流而下,与三阳河水握手,然后滚滚北上,润泽京津。”此外,获省政府评选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有12项。而个人获得先进的更多,除一名烈士外,获得荣誉最高、次数有7次的是陈福坤;而顾宏、李安江、赵方庆、王祖明等有43人次。其中王祖明的爱人是汪老亲戚,如果汪老早年得知,也会夸王祖明干得不丑。
如今,我市以“节水优先”为根本,全面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利用。同时,深化绿色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向长远发展,实现水治理的集成效应,变重建轻管为建管并重,真正发挥水利工程的长久效应。
“悬河”不再是汪老与人们“悬”在心里的一条河,而是“河心塔影流不去”的母亲河,亦是范曾笔下的“悠悠此水钱塘去,即入东坡意匠中”美丽壮阔的河。